红色教育、苦学精神,张桂梅难以复制的神话
红色教育、苦学精神,张桂梅难以复制的神话
6月29日上午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,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、校长,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代表29名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发言。她说:“46年前,我从东北到云南支边,成为一名教师。在无数次家访中,看着一个个山区女孩因贫困失学,我心痛到无法呼吸。我体会到,一个受教育的女性,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,改变三代人的命运。于是,我决心创办免费女子高中,点亮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梦想。”
在建党百年之际,首度颁发的“七一勋章”用以表彰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。在教育战线上,张桂梅和她的华坪女高,改变和影响的不只是华坪一个县城,而是所有大山里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女孩。张桂梅今年64岁,她的身体已经不大好,被搀扶着走进人民大会堂,指关节贴满了膏药。但她说:“只要还有一口气,我就要站在讲台上,倾尽全力、奉献所有,九死亦无悔!”
这是张桂梅,她的开场白是:我叫张桂梅,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11月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的实地采访中,真切地感受了张桂梅是如何通过教育改变当地青少年命运的。以下报道发表在2020.11.23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上。

10月15日,张桂梅在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给同学们讲话。图/IC
张桂梅的华坪女高神话背后
本刊记者/霍思伊
发于2020.11.23总第973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建在半山腰上。
凌晨五点十分,天还没亮,公鸡开始打鸣,间或有一声狗叫,一大片虫鸣声压过来,风在山林间回响,野猫、野狗、蝙蝠还有当地俗称白鼻梁子的果子狸也会出现。校长张桂梅从三楼的一间学生宿舍走出来,打开手电筒,一层层打开楼道里的灯,一有光,这些山里的动物就跑走了。
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此刻开始。
学生们五点半起床,上午五节课,下午三节课,中间午休1小时,晚上分三段,一段2小时,11点半到12点之间熄灯,从周一到周六,每天都是如此。除学习以外,所有其他时间都被尽可能压缩,吃饭不能超过10分钟,跑步往返。张桂梅精心测算过,一分钟约有30个学生打饭,一个年级159人全部打完需要5分钟,最后一个学生也留有5分钟时间吃饭。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周日11点到下午2点,这3小时内,学生们被允许外出,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时光。
乍一看,华坪女高和其他以军事化管理为核心的县中还没有太大差别。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县城里,衡水中学模式被广泛地复制。在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游戏中,对于很多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们来说,以时间换机会是目前看起来最成功、也是现实中唯一有效的思路。
但华坪女高更为成功,或者说更为特殊。在衡中模式里,“名校掐尖”是最关键的前置环节,而女高第一届学生中,很多人中考分数很低,甚至没有达到县城分数线,这些学生在三年后却几乎全部考上本科,本科上线率达到100%。时任云南省副省长李江感慨,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,因为女高的入口极低,来者不拒,没有分数限制。
从2008年成立至今,华坪女高在12年内先后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,一千多个家庭因此脱贫,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百分之百。最新的2020年战绩显示,女高共有159人参加高考,其中150人达到本科线,本科上线率为94.3%。这些数字共同构成了女高神话,也让校长张桂梅在今年成为焦点。
但在感动之余,人们更好奇的是,这个神话可复制吗?

张桂梅身患骨瘤、肺纤维化、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,每日要在身上和手上贴满止疼膏,否则手无法弯曲。摄影/本刊记者 霍思伊
“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”
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、过于理想主义。2004年9月,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,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。途中,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,杨文华坚决反对。在来到教育局之前,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,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,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。而且,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,一直在一线教学,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。
回到华坪后,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,但收效甚微。真正的转机在2007年,她作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党代会。会上,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。张桂梅的“女高梦”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,一夜之间全国皆知。回到华坪后,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,市、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。2008年9月,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,就开始招生。当年的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,市委书记也出席,规格很高,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,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,尘土飞扬。
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。张桂梅有两个要求,一是只招贫困女生,不设分数线;二是学杂费全免。按照她的录取标准,无论分数高低,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,一共有100名女生,此后辍学4名,剩下96名。在听说女高之前,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,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。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,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。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,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。
于是从第二届开始,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,此后一年比一年多。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,实际上,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。面对这种情况,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,因为贫困无法量化。
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说,2014年之前,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,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,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,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。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?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。每年,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,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,也因此,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,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。
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。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这些年,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,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,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,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。虽然有分数线,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。女高每届有三个班,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。
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了解后发现,除了张桂梅本人,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。两轮摩托、房、车,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。
“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,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,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,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,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,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。”张红琼说。据她观察,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。
在杨文华看来,中国国情不平衡,上海的“穷”和华坪的“穷”不可同日而语,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,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。“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。你家里有没有洋房,有没有车,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,有一阵她规定,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,”他说。
女高至今也没有一套制度化体系化的破格录取标准,录取谁不录取谁,张桂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。在县级政府层面,也给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,允许她每年在招生指标外额外录取一些贫困生。“对超出的人数,基本张桂梅上报,县里就会批,”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:“当然也不能超出太多,毕竟女高能招的人数也有限。”
实际上,对于是否划一条明确的分数线,女高内部也有过讨论。但张桂梅认为,“只要划了分数线,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就进不来了,有违女高的初心。”
据女高2015级学生郑珍珍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,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,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。比如她那一届,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,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,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。
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,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,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,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。据杨文华介绍,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,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。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,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,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。
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,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。但学校成立至今,已招收10届学生,每年只能招收100~160人,大多数时候,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。对此,杨文华指出,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,并非不想,而是资金不够。
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。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~4万,包括课本费、资料费、试卷费、高考报名费等,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。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、绿化、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。
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,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。2019年,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.5亿元。据杨文华介绍,12年来,对女高,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.1亿元。
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,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。1990年代,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,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,在2013年之前,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,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,财政收入直线下滑。此后,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,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。目前,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,年产值超过20亿元,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。但芒果属于农业,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,也因此,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。
另一方面,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,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。华坪全县97%的地区是山区,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.4%。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、彝族等少数民族的高海拔地区,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。
女高是边建边招,从2008年到2016年,先后分五期建设,共花费6000万元,其中,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00万元,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,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,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。杨文华说,女高规模小,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,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,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。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,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。
县财政财力有限,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。2020年7月,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,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,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。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,仍然不足。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,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。

教学楼一层的楼道里张贴着女高的捐款人和对应的捐款金额。摄影/本刊记者 霍思伊
由于招生规模不够,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(高)中榜单。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,虽然名为完全中学,即为初中、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,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。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,相当于公认的100强。排名靠前的学校,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。
据杨文华介绍,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,在教学质量上,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、一本率、本科率、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。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,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,且位居前列。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,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;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%,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,以年轻老师居多,职称晋升比较缓慢。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,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。
杨文华认为,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,女高是全免费办学,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,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。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,在他看来,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,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,也能扩大招生规模,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,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。“但她坚决不干。”杨文华说。
在多位受访者看来,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,一旦认定一件事,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,绝不妥协。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,最初要办女高,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,社会影响不好,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,试验一下,她坚决反对,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,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。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,张桂梅坚持,她说,你等得起,孩子等不起。
多年来,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,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,仍葆有不变的天真,“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”。
女高模式
2009年,女高创办一学期后,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。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,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:“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。”
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,山里的孩子基础差,要想出成绩,学生必须要“苦学”,老师更要“苦教”。她面试张红琼时,反复对她强调,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。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,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,张桂梅看她们瘦弱,摇摇头。
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,学校面临崩溃。最艰难的时候,张桂梅发现,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,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:“如果是在抗战年代,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,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。我们剩6个党员,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?”会后,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,然后面向党旗,宣誓。所有党员都哭了。
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,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。从这一刻起,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此前,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,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。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,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,要想留住老师,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,培育奉献精神。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,毋宁说,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问张桂梅:“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,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,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?”
她说:“两者都有。”
从效果看,这种策略是成功的。在张红琼的回忆中,这次会议之后,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。每天下午五点半,学生们在吃饭,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《红梅赞》,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《江姐》的主题曲。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,“三九严寒何所惧,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”。最初,张红琼觉得很尴尬,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,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,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,大家都在唱,也不觉得奇怪了。“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,后来甚至会跟着唱。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。”她说。

7月4日,张桂梅用喇叭催促学生打扫操场。图/新华
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,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。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,学生去食堂吃饭时,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。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,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。
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,记者在现场看到,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,先集体朗诵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,然后大声喊出口号:“感党恩,听党话,跟党走,做党的好女儿”“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”“奋斗、奋斗、再奋斗”。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,第一首是《英雄赞歌》,这是电影《英雄儿女》的主题曲,第二首是《红色娘子军》。此前还曾跳过《南泥湾》和《红梅赞》。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,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,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,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。今年,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,在跳第三套操时,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,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《山里红》。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,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,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。
从2010年开始,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,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,然后齐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每学期开学时,全体师生要抄党章。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,由张桂梅亲自执教,最长时可能持续2~3小时。课上,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、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,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。每周日晚上七点半,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,既有经典老片《孔繁森》《焦裕禄》,也有新片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除电影外,还会每周追剧,让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《雪豹突击队》,“当时每周看一集,我们都边看边哭。”
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。最初,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,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“巨无霸”党旗,旁边立着“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”几个红色大字。“非常壮观,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,这么大一面党旗,你站在下面,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。”张红琼这样感慨。
和学生的作息接近,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。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,如果有早自习,她要五点多起床,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,中午11点下班后,吃个饭,12点就要回来,下午课从2点开始,五点半结束,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,6点继续上晚自习,直到11点半,天天如此。张桂梅要求,无论有课没课,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,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。
在女高,老师结婚、怀孕都不是偷懒“摸鱼”的理由,想请长假很难,建校至今,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。2014年,张红琼怀孕了,但还要管全校卫生,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。为躲避扫地,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,张桂梅就批评了她。对此她回忆说:“当时,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。后来孩子一岁多,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,她说,你是一个老师,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,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。”
有人问张桂梅,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,老师年轻,高考成绩还那么好?她毫不犹豫地说:“因为我们能吃苦,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。”
2011年,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,震惊了整个县城,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“学习女高精神”,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,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,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。
但胥国华也坦言,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,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。“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,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。”
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,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当时,华坪一中学习女高,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、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,要给学生义务答疑。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,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,不出席就算旷课,进行处罚,“结果收效很明显,老师对学生的成绩、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,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。”他说。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。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,便很快放弃。
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,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。一天晚上,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。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,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,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,很受触动,也很羞愧。“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,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,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,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。”她这样说道。
实际上,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。张桂梅丈夫早逝、没有子女、没有房和车,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,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,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。她事必躬亲,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。
张桂梅只有一个,从这个角度而言,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。作为旁观者,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。多位一中老师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,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,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,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。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,就是张桂梅。
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,张桂梅之后,谁来执掌女高?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,身体状况也不佳,身患骨瘤、肺纤维化、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,2019年初,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。今年春节,她再次病危入院。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、县政府领导后发现,对于女高接班人,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。

9月3日,华坪女高学生列队进入操场参加活动。图/新华
教改与培训
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,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、清华。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,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个环节,所有学生要齐喊:“加油!上清华!加油!上北大”。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“北大清华我来了!”背景是列队整齐的学生在操场跑步,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。
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。张桂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坦言,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,不是她们不努力,而是成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,够不到最顶尖的名校。目前,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,靠得就是下死功夫。其他学生也是如此,一本课本5、6遍地背,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。“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。”她着急地说。
张桂梅最初以为,女高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,只会僵硬背诵,需要“一个老师帮她们点一下”。她咬咬牙,请长沙的一位名师来女高讲课,一天给3万元课时费。这位名师带过的毕业班中,有一半考上清北。“我不吃饭也要把这些老师请来。结果他来了以后,啪啪讲完,学生们都傻了,一点也听不懂。是他讲得太高深了吗?还是他的思维太超前?都不是。但他给他的学生们可以这么讲,我们的孩子就不行。”
杨文华对此解释说,这没什么好奇怪的,“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师来华坪教课,也会把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涂。他对这些学生的基础薄弱情况、学习和行为习惯都不了解,用针对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那一套来教大山里的学生,这些学生听得懂吗?”
于是,张桂梅意识到,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,而是“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”。无论是外地名师,还是名校的大学生志愿者,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困境。“请进来”并不是破局之法,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。
与“请进来”相比,杨文华认为,“走出去”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。他指出,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,外出培训不够多。相比之下,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训,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。
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,曾去临沧市参加培训。他说,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,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,而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,激发教师去思考,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,如何提高自身素质。
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,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,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数量少,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,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,还要管生活。杨文华则认为,这虽然是原因之一,但并非无法克服。实际上,在师生比上,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加紧张,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;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,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,平均下来,每位老师对应的学生不超过12名,比一中还少一些。
在杨文华看来,张桂梅不鼓励女高老师外出培训,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女高老师们“思想滑下去,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”。“比如,外面学校的老师待遇更好,而女高是个讲奉献的地方,如果送出去后心收不回来怎么办。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,某某学校把我老师的心搞乱了。我就和她说,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么坚定,百毒不侵,你怕什么?”

9月2日晚,华坪女高学生临睡前在宿舍楼道里复习。图/新华
师资难题
女高的“死结”折射出当代乡村教育的典型困局。核心问题指向两个,一是学生的基础太差,二是县中师资匮乏。这二者互相影响,互为因果,形成恶性循环。
在女高教师张红琼的地理课上,过于尴尬的安静已经持续了五分钟。半小时前,她在黑板上写下这节课的讨论主题:如何在现实中理解热力环流?将学生分组后,她们“讨论”得很热烈,但轮到发言环节,组长站起来,一个字都挤不出来,这是2011年前后。
不久前,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丘北中学的老师来到女高,提出“自主讨论”的教育改革理念,张桂梅于是将每节课从45分钟延长到一小时,规定老师只讲半小时,剩下半小时由学生自主讨论,借此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和举一反三能力。同时,这也被视为女高由传统教学模式向素质教育短暂靠拢的实验。
但张红琼在实践中发现,女高学生基础差,缺乏自主讨论的能力,即使给她们足够的时间,也只会在课堂上聊天,并不会真的去碰撞和思考问题。她发现,“很多学生进到高中后在地理上基本是零基础,小学初中仿佛没有学过,连经纬线都不懂,更别提七大洲四大洋,你问她们美国在哪儿,根本指不出来。”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两个月后,张桂梅叫停了改革,失败让她更加坚定了“苦学”的教育理念。“没办法,我们学校只有花这么多时间去学、去教,人家学校是三年高中,我们还要把初中甚至小学九年的知识都补回来。”张红琼无奈道。
2015级女高学生郑珍珍是村里第一个女高学生。她所在的村叫白姑河村,是一个典型的傈僳族村寨,位于华坪县通达傈僳族自治乡。通达乡距离县城50公里,山路曲折,开车大约要2小时,海拔在1562~3198米之间,下属的大多行政村都非常贫困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在白姑河村走访时发现,一直到今年,全村只出过三个高中生,都考上了大学。其他村的情况也是如此,考上高中的孩子凤毛麟角,很多村尚未走出过一个高中生和大学生。在这些高中生中,女生大多在女高就读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孩子辍学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成绩太差,考不上高中,而并非因为贫困或观念落后。即便是在还没有通路的村寨,教育观念也已经有很大改变,以前村民们觉得读书没那么重要,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,现在父母都希望孩子可以好好学习,考上大学,“但小孩读不进去,父母干着急,一直催他,给他压力,也没用,”多位通达乡村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无奈地说道。
在和村里的辍学儿童交谈后发现,在外界看来,大山里的孩子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,但实际上,这些孩子却相反,很多都非常厌学,哪怕逼迫自己在心里重复“知识可以改变命运”,却无法将它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勾连。即使是女高学生,在读高中前也非常懵懂。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选择去女高,只是因为不想回家种地。“读书能干什么,读书对你有什么影响,也没有想过外面是什么样子,对什么都没有意识和概念。”她这样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通达傈僳族自治乡潘兴陈总结女高模式时,特别指出,张桂梅的聪明之处,通过红色教育让学生对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,给自己一个更明确的定位。这点对大山里的孩子尤其重要,是想办法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对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渴望,让她们产生内生动力。
在潘兴陈看来,华坪的学生基础差,主要是因为小学和初中的师资匮乏。
通达乡丁王村民族小学(简称丁王民小)是乡镇里最好的小学,来自附近四个村子的278名学生都集中在这里就读,学生以傈僳族为主。
丁王民小校长蔡文璐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学校的老师以本地人为主,大多是考出去后出于“回报家乡”的心理回来任教。事实上,通达乡这些年考到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也不少,但回到华坪县城的都很少,更不用提乡镇。他指出,工资少只是一方面原因,山区的老师都要有点奉献精神,“撤点并校”后,学生家离学校太远,很多小学和初中都是全寄宿制,老师既要负责学生的学习,还要操心生活,负担很重。县城的老师每天还可以回家,乡镇上的老师则要和学生一起同住,每周只有一天可以回家。也因此,乡镇学校教师流失的情况非常严重,“越优秀的人才流失的越快。优秀的老师都想要往县城调,或者是去丽江和昆明这种大城市。”他说。
蔡文璐还表示,目前学校能招来的正课老师以二、三本为主,音乐、美术和体育老师则根本招不齐,很多副科老师都是身兼数职。事实上,对于整个华坪县的所有中小学来说,招聘老师难是个未解的“死结”,且近几年情况越来越严重。
杨文华指出,县中招老师,“985”“211”的学生根本不考虑,因为招不来。以华坪一中为例,以前招聘的要求是一本,后来门槛降到了二本,现在三本也可以录取,一降再降。女高则不愿妥协,只招一本以上的老师,因此招聘难的问题格外突出。
从2008年成立至今,华坪县给女高的老师编制47人一直没有招满,目前学校在编教师共有40人。今年9月,女高再次面向全国急招教师7名,具体包括语文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生物和地理教师各1名。招聘要求则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、双一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,一旦聘用,在女高的服务期要不少于六年(含试用期一年),且六年内不得调出。在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眼中,这个条件极其苛刻。
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招聘信息挂出去半个多月,来报名的只有1个,后来又陆续有一些报名,但都不符合条件,最终录取的只有1名。杨文华认为,包括女高在内,县城中学现在最缺的还不是硬件,实际上,所有硬件的升级和更新换代最终都要靠老师去操作。整个县城的教育生态要想有质的变化,关键还在师资。
(文中郑珍珍为化名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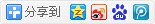
 龙王办事处球赛
龙王办事处球赛